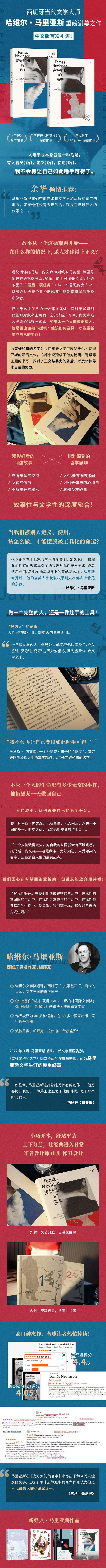
故事,从一个道德难题开始——
在什么样的情况下,杀人才称得上正义?
退役间谍托马斯·内文森回到故乡马德里,试图修复破碎的家庭关系。然而,前上司图普拉找到他并提出“蕞后一项任务”:从三个普通的女人中,找出并处决那个曾协助恐怖组织制造惨案的隐藏身份者。
内文森以英语教师的身份接近三人,试图找出蛛丝马迹,但关于这次任务的一切都很模糊。面对难以甄别的目标和图普拉的“全部清除”命令,内文森陷入巨大的犹疑与焦虑:如果杀一个人能救更多人,他是否应该扣下扳机?他该如何选择,才能重新掌控自己的生命?
一个拒绝成为棋子的“幽灵”,渴望回到虚无人生的真实起点,找回他完好如初的名字。
当个体被裹挟于不可见的战争,如何在忠诚与背叛、行动与良知间寻找支点?小说延续了马里亚斯对秘密、谎言等主题的书写,探讨正义与暴力的矛盾,以及个体寻求自我的努力。《完好如初的名字》以其冷峻的深度与悲悯,成为马里亚斯文学生涯的厚重终章。
哈维尔·马里亚斯
Javier Marías
西班牙著·名作家、翻译家,1951年生于马德里。1979年因翻译《项狄传》获得西班牙国家翻译奖。1992年出版《如此苍白的心》,英译版于1997年获得IMPAC都柏林国际文学奖。另著有长篇小说《万灵》《明日战场上想起我》,短篇小说集《不再有爱》等。
2022年9月11日于马德里病逝。
圣德尼在被罗马帝国皇帝瓦莱里安追捕时不幸殉道,惨遭斩首,他把自己被砍下的头颅夹在腋下,从蒙马特一直走到了埋葬他的地方(这极大减轻了搬运工的负担),足足走了九公里,后来那里建了一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修道院或堂。这桩神迹令这位红衣主教目瞪口呆,他保证此事千真万确,但实际上他在转述时没少添油加醋,一位听故事的聪明女士打断了他,只用一句话便让这件英雄事迹大打折扣:“啊,主教!在那种情况下,难的只是第一步而已。”
难的只是第一步而已。也许,这句话放之四海而皆准,或许至少适用于那些需要付出努力,而人们带着不情愿、厌恶或保留态度去做的事。我们能毫无保留地去做的事少之又少,我们几乎总会因为某种原因无法采取行动,迈不出那一步,出不了家门,动不了身,不跟任何人交谈,也避免别人跟我们交谈、盯着我们、告诉我们一些事情。有时我觉得,我们这一生——包括那些野心勃勃、躁动不安、急切贪婪、渴望干预甚至统治世界的人——只不过是一种存在已久却迟迟没有实现的渴望:渴望回到我们出生前那种不被察觉、不被看见、不被听见、不会释放出任何热量的状态;渴望沉默和安宁,回溯我们走过的路,撤销已成定局、无法挽回的事,以及那些只有足够幸运才会无人提起、被人遗忘的事;渴望抹去能证明我们过去存在过的一切印记。遗憾的是,这些印记仍然在一段时间内存在于我们的现在与将来。然而,我们无法实现这种连自己都不承认的渴望,或者只有某些勇敢、强大、几乎丧失人性的人才能做到:那些自杀的人,隐退和等待的人,不告而别的人,彻底隐匿的人——那些真正永远不想被找到的人;天涯海角的隐士,摆脱旧身份(“我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我了”)并毫不犹豫地接受新身份的人(“蠢货,别自以为了解我”)。逃兵、流亡者、篡位者、失忆者,那些无法回忆起自己本来的面目,并说服自己相信不再是出生时、年幼时、年轻时的样子的人。那些回不去的人。
最难的是杀人,这是没有杀人经历者尤为认同的常识。他们这样说是因为无法想象自己拿着手枪、尖刀、绳索或砍刀的场景,大多数犯罪之举都需要时间,需要铤而走险(我们的武器可能会在争斗中被对方夺走,最后没命的是我们自己),如果是近身肉搏的话,还需要有体力。但人们早已习惯于在电影里看到角色使用配有瞄准镜的步枪,只需扣动扳机便能命中目标,干净利落、几无风险地完成任务。现在,有人能在距离目标数千公里之外操控无人机,终结一条或数条性命,就好像这一切是虚构的,是想象的行为,就像是电子游戏(在屏幕上观看结果),对于那些老古董来说,这就像是打在翻板上的大钢珠。没有任何风险也不会出现鲜血四溅的情景。
人们认为杀人很难,还因为结果无法逆转,一旦做了就成定局:杀人意味着死者什么都不会有了,他不会再做任何事,他思维的河流枯竭,思想的明灯熄灭,他无法改正、无法弥补、无法挽救任何伤害也无法被说服;他将永远不再说话或行动,没人能再指望他做任何事,连呼吸和睁眼都不行;他会变得完全无害,或者更糟,变得毫无用处,仿佛一台变作碍事玩意儿的坏电器,一件碍手碍脚、必须挪开的废品。大部分人都觉得杀人过于极端、激烈,他们倾向于认为所有人都能被救赎,在他们内心深处相信所有人都能改变和被原谅,相信瘟疫会自行消失,无需我们来消灭。而且,我们对他人会有难以言喻的怜悯,我怎么会结束别人的生命呢。然而,面对现实时,怜悯之心会减弱,有时甚至会突然消失——哪怕我们自己没有粗暴地遏制这份怜悯。
Copyright 版权所有 © jvwen.com 聚文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