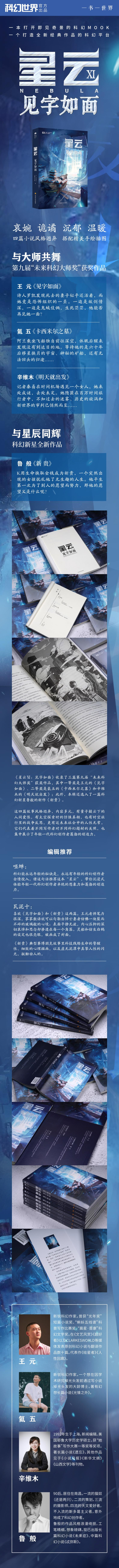
他们劝我节哀顺变。 还好吧,我并没有歇斯底里,没有哭天抢地和捶胸顿足,我很平静。 人固有一死。她去了天堂。不必拿这些敷衍的安慰话搪塞我。很难说清楚这种感受,更多的是空白,提笔忘言——我曾无数次面对一张白纸,静默整夜;碎裂的想法在空中飘浮,思绪像含羞草的叶瓣,碰触只会制造闪躲和闭合,不如远观。 此刻,我坐在灵船上,端详中的妻,她神情安详,睡着一般。过去我夜半惊醒,看到床头灯洒下的橘黄色之中就是这样一张不动声色的脸。她穿着白色长裙,双手叠放在腹部,掌心压着一本诗集,我的诗集。她的父母和亲朋环绕在棺椁周围。仿生白鹤不时传来阵阵清唳,为轻缓的背景乐和声。我擅自做主,把哀乐替换成一首古老的流行歌曲《稻草人》,这是我跟妻甜蜜爱情的见证。 透过舷窗眺望,飘浮在空中的墨城A-3区灵堂已显露轮廓。那将是她的归宿。灵堂风格复古,跟灵船一脉相承。灵船外形复刻自一艘明朝官船,顶层覆盖琉璃瓦,两侧各有一双竹竿与帆布制成的机翼,当然,只是用来调节方向,真正的动力装置埋藏在船底控制室。这是一艘名副其实的飞船,飞在空中的船。至于灵堂,更像一座中式堡垒,一圈圈的房屋叠凑,凸出的屋檐由斗拱支撑,雕梁画栋,器宇轩昂;四周各有一座玲珑宝塔,寄存骨灰盒。乍一看,不像灵堂,倒像天宫。 如今,死去的人都到了天上,这再也不是一种单纯的修辞。 我其实挺排斥这种场面,不管是婚礼还是葬礼,在我看来,都有些形式大于内容,那些被传统观念辐射的参与者大多抱着应付差事的心态,婚礼和葬礼只对一两个人的生活产生实质性影响。我真想把他们赶下灵船,一脚一个踢到空中,包括她的父母,我不愿和任何人分享她的最后一程。大部分来宾甚至不如司仪投入——他一袭牧师黑袍,与中式丧葬氛围格格不入。或许他真的是位牧师,主持完葬礼就要去教堂聆听告解。我不信这套,不管祈祷还是超度,都不能让妻回生。 死亡不是为逝去的人准备,而是为活着的人张罗。 灵船泊入港口,白鹤悬停半空,铺出一条肃穆甬路。送葬者跟随司仪上岸,步入告别大厅。工作人员把推到厅前,在周围布满绢花,妻的全息影像从棺中浮出,宛如魂灵出窍。她平时不苟言笑,我翻遍云端,才拾得几帧欢乐的动图。 她笑得真美,我的心都要化了。我们被要求围绕遗体逆时针转三圈,之后垂首聆听司仪的葬词。 “今天,我们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告别史婧女士,她是孝顺的女儿,是贤惠的妻子……” 瞻仰遗容,最后一次看她,我咬紫了嘴唇。 送别时刻到了。 我常常用两行俳句自勉:随时准备面对死亡,只要活着就感谢上苍。我现在仍然要感谢上苍,死去的人是她,若不然,她该有多恨活着。唉,我有些想当然,如果躺在里面的是我,她也会顺着过去的轨迹一如既往地向前滑行吧。 落入熔炉,换回一抔温热的骨灰。灵船压抑的氛围终于被引爆,人群像一朵窝藏惊雷的乌云,响起此起彼伏的哭声。岳母泪如雨下,悲痛欲绝。岳丈假装沉着,悄悄用手背擦拭眼角。我没有任何反应,那一瞬间,我是死的。酩酊之人一定有过以下体验:从饭店出门,坐车,呕吐,脱衣,上床,自己对这一系列行为都有印象,一觉醒来却无法回溯醉酒经过,一切仿佛一场失重的梦。我当时就是烂醉如泥的酒鬼,身边正在发生的一切都与我有朦胧的距离,我身处葬礼的中心,却毫无参与感。灵船起飞,白鹤送行,大厅送别,火化成灰,灵堂安息,整个葬礼忽远忽近,我都不知怎么回到家中的。 回到家中,客厅电视墙糊着一张白纸,上面用楷书写着一个“奠”字。不知怎的,看着那一笔一画,一撇一捺,墨色在宣纸上洇开的毛刺,我突然泣不成声。 我以为我很平静,我以为我不难过。 我以为。 3 我其实挺排斥这种场面,诗人都是孤独分子,但黑纸白字写进合同,乙方有义务配合甲方宣传。我坐在椅子上,像待价而沽的商品。其中一个环节,读者朗诵诗歌。他们手捧散发新鲜油墨味道的诗集,挑选心仪的几行,或情绪饱满,或冷静平淡。作为诗集的创作者,我也被邀请到舞台中央。我有些胆怯,他们的目光鼓励我,别不好意思。我深吸一口气,微微闭上眼睛,只能感受到模糊的光,无法视物。光晕之中,我仿佛看见史婧,她像往常一样慵懒地窝在沙发上,手握一支铅笔,在纸上沙沙地计算,或者补数独游戏的空。猫在沙发靠背上轻巧地踱步,走到尽头,拱起脊背,笼出一个巨大而无声的哈欠。 我曾和你在一起 在黄昏中坐过 在黄色麦田的黄昏 在春天的黄昏 我该对你说些什么 我声如蚊蚋,小心翼翼,如初次行窃的小偷。这是我为史婧写的第一首诗,记录我们初次相遇的傍晚。她瞥了一眼就扔在茶几上,继续在数字的海洋里徜徉。 P4-6
Copyright 版权所有 © jvwen.com 聚文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