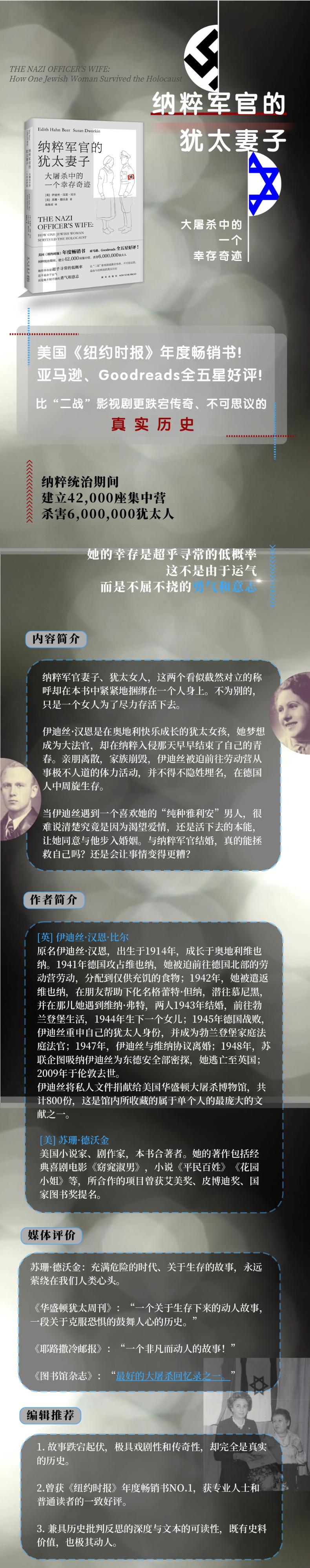纳粹军官的犹太妻子 大屠杀中的一个幸存奇迹
- 字数: 211000
- 装帧: 平装
- 出版社: 新星出版社
- 作者: (英)伊迪丝·汉恩·比尔(Edith Hahn Beer),(美)苏珊·德沃金(Susan Dworkin)
- 出版日期: 2020-05-01
- 商品条码: 9787513337915
- 版次: 1
- 开本: 32开
- 页数: 327
- 出版年份: 2020
定价:¥52
销售价:登录后查看价格
¥{{selectedSku?.salePrice}}
库存:
{{selectedSku?.stock}}
库存充足